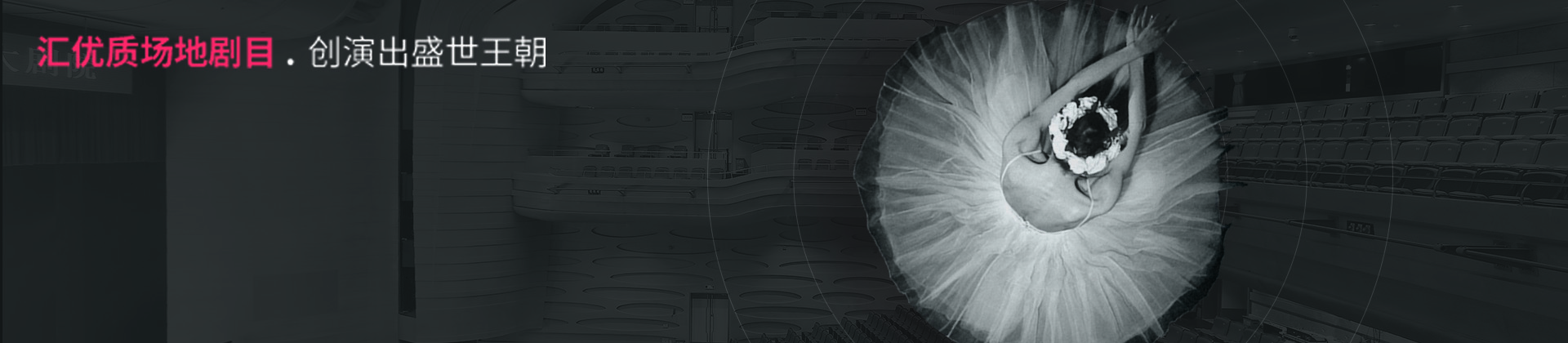“真实的生活,其实比‘超现实主义’更‘超现实’。”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努里・比格・锡兰6月20日亮相主席论坛,与来自各国的青年影人聊电影创作,他表示镜头能赋予观众更多层面的思考,这就是电影的魅力。
锡兰是土耳其国宝级导演。2011年以《小亚细亚往事》拿下戛纳评审团大奖,2014年以《冬眠》拿下金棕榈奖,对许多中国观众来说,他是欧亚大陆艺术电影的一面旗帜。锡兰透露在自己的创作中,大师和经典是他不尽的力量源泉,他喜爱契诃夫,在电影中,“我会通过他的眼睛,过滤这个世界”。
镜头对准熟悉的乡间,在电影中重塑生活不容易
锡兰擅长用深沉悠长的镜头,展现土耳其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,以及平静表面下人们精神生活的暗流汹涌。谈到为何将镜头专注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乡间,从不考虑异域的风景,锡兰表示,艺术创作的说服力应该来自于生活,电影必须增加丰富真实的细节,闻得到生活的气息,才能说服观众。
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锡兰最新力作《野梨树》,创作视角就受到他回乡探亲之际,重逢一位退休老师的影响。锡兰过去非常敬重这位老师,他和锡兰父亲一样,一辈子在村里务农,对大多数人都很陌生疏远,也不被周围的人喜欢。“从他们身上,能看到土耳其农村社会的残酷一面。我想用电影对这些价值观提出一些问题。”锡兰向退休教师的儿子提出,能否写一些对他父亲的回忆。三个月之后,他收到了满满八页的故事。――这些书信成为了锡兰创作《野梨树》的重要素材。
“在电影中重塑生活是不易的,观察、理解、认识生活的细节,你需要对文化、政治、历史有深入的了解。”锡兰透露他在上海博物馆拍了许多照片,回家发现很多展品乍一看风格很类似,深究细节,其实都各不相同。同理,艺术家也可以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创作,结果却会千差万别,如此才能百花齐放。“导演独特的表达方式,体现了对生活的直觉和思考。”
大师和经典是滋养,导演要把一些内容藏起来,让观众去探索
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主席及评委作品展,是锡兰在中国大陆首个完整个人回顾影展,加上一部短片作品《茧》,共展映他的九部电影。锡兰并非高产的导演,他说:“每拍一部作品,它就会改变我,为我找到方向,去拍下一部电影。”对他而言,灵感来自各处,没有公式可言,就像河流中的水滴,慢慢集聚,汇成了奔涌向前的滔滔激情。
在锡兰逐渐享誉国际的前行道路上,大师和经典,正是他不尽的力量源泉。“契诃夫所有的戏剧和诗篇,我都读过很多遍。”除了向契诃夫遗作《樱桃园》致敬的《五月碧云天》,锡兰告诉记者在他所有电影中,“都能看到契诃夫的影子”。
或许是文学深厚的滋养,让锡兰的电影中不乏哲学性的大篇幅对白。那么,这是否会使观众感到烦闷?锡兰回答:“所有类型的电影都会使部分观众感到无聊,所以‘无聊’不该是导演考虑的问题。导演应该考虑的,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议题,它对别人来说可能也具有重要性,如此就能找到电影的受众。”
锡兰将文学对话比作一场“游戏”,它确实因为和现实生活存在距离,很难在电影中呈现,但其中的真实和隐瞒,能丰富地展现人物性格,甚至成为华彩段落。在这方面,陀思妥耶夫斯基堪称锡兰电影创作的艺术指导:“我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大论的对话,它们精彩地展现了人性,并且启示我:导演不仅要让观众看到一些内容,还要把一些内容藏起来,让观众自己去探索。”
在留白的部分,锡兰擅长用声音给观众提示。“布列松说过,如果可以用声音讲故事,我们就不必用画面展示出来。”在大师的影响下,锡兰养成了必须全权把控每一个声音细节的考究。他会从成千上万种声音中找到独特的一种,引导观众理解电影叙事。
寄语电影新生力量:在调整和尝试中,期待艺术的偶然奇迹
锡兰说,拍摄电影是他摆脱孤独的方式。他坦言,“我是一个很忧郁的人,如果不是因为孤独,我不需要用电影去创造生命的意义。”
锡兰透露了自己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。他从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,花了两年时间在米马尔希南艺术大学学习电影,又度过了将近十年的迷茫岁月。“那个年代,摄影只能作为一种业余爱好,很多人不认可靠艺术谋生。”锡兰在大学毕业后留学伦敦,找不到未来职业方向,只能从餐厅服务员做起……他鼓励年轻影人:“恐惧能转化为你的动力源泉,不要被害怕打倒,继续孤单地前进吧。”
锡兰表示,生在数字时代的年轻影人是幸运的,数字拍摄给予艺术创作更多可能性。“从我拍摄第一部电影开始用的都是胶片。胶片太昂贵了,演员压力很大,一点小错就会耗费几百美元。同一个镜头,当时可能最多拍三遍,而有了数字拍摄可以拍几十遍,在调整和尝试中明确自己想要的艺术效果,期待一个偶然的奇迹。”(本报记者 吴钰)
【原文发布地址】:http://www.cnr.cn/ent/zx/20190624/t20190624_524661064.shtml